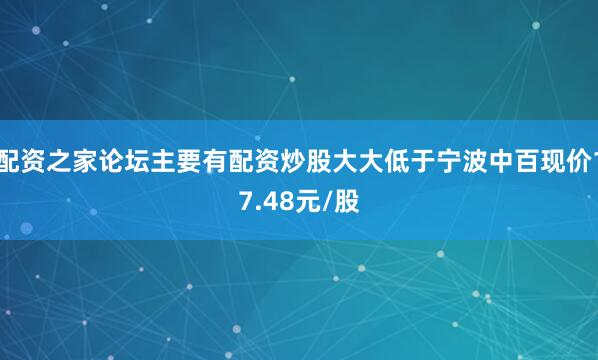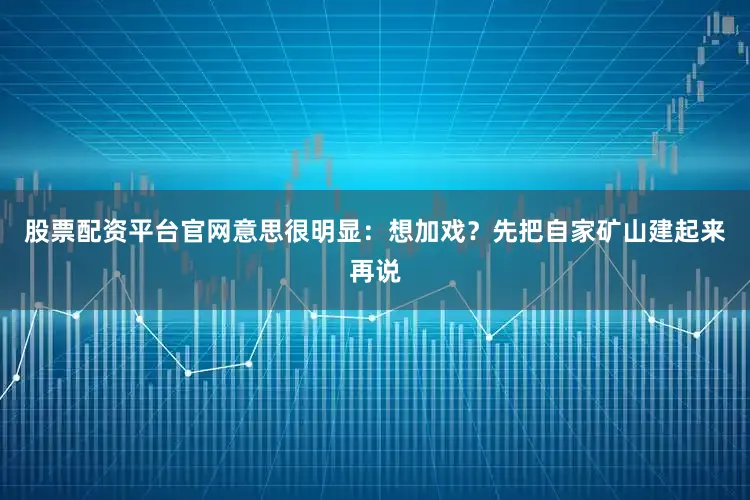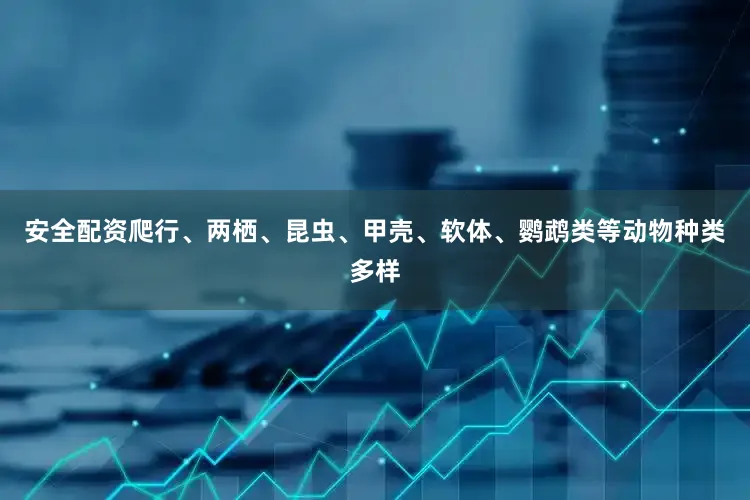贝鲁特南郊的天空,像是被一年前的硝烟染上了永久的灰色。哈桑・纳斯鲁拉的墓前,成千上万张面孔汇成一张巨大的表情,上面写满了两种情绪:悲伤,以及比悲伤更滚烫的愤怒。
人群的最前方,接替了纳斯鲁拉位置的纳伊姆・卡西姆,声音像是从胸膛里砸出的石头:“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武器,也绝不会交出武器。”每一个字都重重地敲打在现场每个人的心上。
那具冰冷的墓碑下,埋着旧时代的和平
这不只是一场悼念。这更像是一场宣战,向那份早已名存实亡的停火协议宣战。卡西姆甚至喊出了“我们已做好殉道的准备”这样的话。现场,真主党那标志性的黄旗,与黎巴嫩、巴勒斯坦、伊朗的国旗混杂在一起,翻滚着,像一片愤怒的海洋。

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慷慨激昂的战歌,人群中“美国去死,以色列去死”的口号,一浪高过一浪。一年前纳斯鲁拉的死,几乎折断了真主党的脊梁,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黎巴嫩政府甚至都开始盘算着,怎么把他们的武装给解除了。
可眼前这一幕,却像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停火?别开玩笑了。谁想要收走我们的武器,那就准备好用命来换。
停火协议?擦屁股都嫌硬
所谓的“停火”,不过是强者给弱者画的一张饼,看饿了,却不能吃。就在十天前,9月18日,以色列的战斗机又跟逛自家后院一样,在黎巴嫩南部上空呼啸而过。迈斯杰贝勒、德宾、泰卜尼特……一连串边境小镇的名字,在几小时内就跟火光与浓烟联系在了一起。
以色列军方的剧本,十年如一日,毫无新意。先假惺惺地“提醒”平民快跑,然后就用炸弹告诉你他们不是在开玩笑。理由还是那个老掉牙的借口:打击“真主党精锐部队的武器存放点”,直到“威胁消除”。
这套说辞,等于把黎巴嫩的国土变成了以色列的专属靶场,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黎巴嫩总统约瑟夫・奥恩的回应,与其说是愤怒,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哀嚎。他痛斥这是对主权的公然践踏,更是把矛头直指当初的担保国。
他说,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法国,用可耻的沉默,“默许了更多的侵略”。从去年11月协议签下的那一刻起,和平就只活在纸上。以色列的空袭从未停过,边境上还钉着五个驻军点。那份停火协议,早就成了一张可以随时被丢进火堆的废纸。
枪杆子才是唯一的家人

以色列的逻辑简单粗暴:真主党在黎巴嫩,所以黎巴嫩就是威胁,就可以炸。而真主党支持者的回应则更加直接:你越是威胁我,我手里的枪就握得越紧。
51岁的维萨姆・霍德罗伊,特意从伊拉克赶来参加纪念。“上次战争后发生的一切,没有削弱我们,反而让我们的信念和力量更加旺盛。”他激动地说,“在武器问题上,没有商量的余地!”
这种决绝,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传播。21岁的大学生阿里贾法尔说,让真主党交枪,这是敌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。就连18岁的女学生扎赫拉海达尔,眼神里也透着与年龄不符的坚定:“我们绝不会向敌人屈服。”这种情绪不是凭空来的,是刻在骨子里的血泪记忆。
一个值得玩味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——伊朗安全负责人阿里・拉里贾尼。作为真主党背后最坚实的靠山,他的到场,本身就是一个无需言说的信号。这份来自德黑兰的底气,正是真主党敢于和以色列及美国叫板的资本。
牌桌上,从来不止两个人
这场游戏的玩家,远不止以色列和真主党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五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,简直是把虚伪和霸道演绎到了极致。他嘴上夸奖黎巴嫩政府为解除真主党武装“所做的努力”,下一秒就话锋一转,冷冷地强调,他要的“不只是口头承诺”。
这等于直接把刀架在了本就摇摇欲坠的黎巴嫩政府脖子上。贝鲁特的政客们处境尴尬到了极点。一边是来自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巨大压力,逼着他们制定计划,去解除真主党的武装。
可另一边,真主党是黎巴嫩内战后唯一合法保留武装的派别,其势力早已渗透到国家的每个角落。让一支连自己国家都未必能完全掌控的政府军,去收缴一支可能比自己更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武器,这听起来就像一出政治笑话。黎巴嫩总统奥恩呼吁建立“统一的国家、强大的军队”,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这更像一句无力的口号。

结语
绕了一圈,所有问题又回到了原点。停火协议是外交官们用来装点门面的辞令,而战斗机和导弹才是这片土地上通行的语言。那些所谓的担保国,更像是站在牌桌边看热闹的闲人,偶尔动动嘴皮子,却从不真正下场。主权在这里,轻得像一片羽毛。
轰炸过后,废墟上总会再次升起炊烟,孩子们也总能在尘土里找到新的游戏。生活在继续,但那份随时可能被爆炸声撕碎的恐惧,像一个巨大的阴影,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。所谓的和平,也许真的只是下一场战争来临前,那一段短暂得令人心碎的喘息。
同创优配-配资开户大全-股票开杠杆-配资炒股导航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